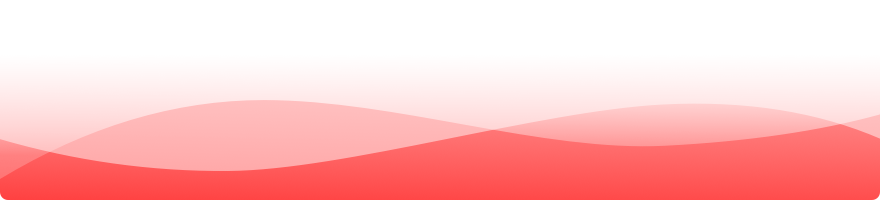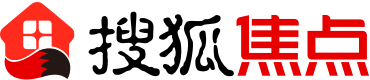长安山下 | 弦歌盈耳长安山
扫描到手机,新闻随时看
扫一扫,用手机看文章
更加方便分享给朋友
正如丽娃河是沪上一所大学的代称,长安山则是闽地一所大学的别号。据说,校园的一山一水,往往只对她的学子,尤其是后来成了“游子”的学子有特别的意义,那些风物浸染了乡思,编织着关于母校的记忆和认同。
此时,校园和风物同构为余韵悠长的象征。“游子”们站在外头或缱绻或伤怀,在他们尚未远离时,这通常是难以体会的,而对于“局外人”来说,大约压根就不想理会。
大学的人文和它的风物之间实在是谜一般的关系。到底是大学滋养着风物,令其卓尔不群,还是风物特有的灵性作为不可或缺的要素涵养着大学?解开这种疑惑虽非一蹴而就,细思起来却别有一番意味。
大学的风物无外乎两种。
一种是长安山这样的,从一纸白板开始的涂绘,因为起初的“一穷二白”,甚至迄今也不太引人注目。
另一种是湖南大学的岳麓书院那样的,巨大的遗迹携着辽远的历史矗立于校园,只有不愿深究的人们才会津津乐道,仿佛它和大学是美妙的二位一体,仿佛现代建制的大学得天独厚地赢得了某种机缘,硕学鸿儒和莘莘学子在这片古今连通的方域俯仰自得、问道求学。它来自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承袭。
也许是一次无心插柳的校址的勾划,也许是漫长的、几经迁徙之后的缓慢落定和汇合。这是一种幸运,更是一种负担。跌宕起伏、一唱三叹的历史风华如何在不断延续、展开的时空,被卓有成效地承前启后并发出新枝,给景观镌刻上今时今世的投影和心跳,这才是人文化景观的真义。
怀抱岳麓书院的湖南大学,必得面对曾张大到优质的辉煌,固然,我们愿意对继往开来寄寓热望,如果大学以朝乾夕惕的态度,仰仗绝大的智慧寻觅创生的结合点,当可以在历史与现时的交汇中结出硕果。
无论如何,历史掷出的回声是无法掉以轻心的压力,在它上面添砖加瓦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。
倘若北京大学始终近距离地望着皇城根,守着红楼而不迁往西郊的燕园,不在一片荒野中辟出一镜人工湖,垒起一幢蓄水塔,大概不会有如此轻盈的超脱为精神化的未名湖和博雅塔,对它的描画,或许还得沉浸到更复杂、滞重的区位左右盘桓吧。
平地起高楼没有了历史的羁绊,却要一代又一代的“白手起家者”不绝如缕地进取,把自己熔炼为历史本身,化作绵绵的人文气息。
长安山毕竟不是未名湖,龙头老大的北京大学轻易地聚集了一茬茬的大家巨子,如此夺目地在风云际会中一次次地擦亮湖面——那闪耀的精神,它的光芒不可阻遏也难以掩蔽,终于被读作大学应有的象征,供人追摹、省思和借镜。
长安山只能不温不火,默默地层垒着自己的精神标高,缓慢地加入并修正这座名为“三山”的城市的定义。它在 “三山”之外的格局,既被地理方位决定,让它远离旧城,也被历史文化限制——毕竟,城市史着意钩沉的多是与时势浮沉起伏密切相关的人和事,以及环绕着“建城史”的庙宇府衙、深宅大院。
它孤悬于乌山、于山和屏山的远处,后者以乌塔、白塔和镇海楼为福州构形,筑起不无傲慢的中心与边界,让有着厚重历史的摩崖石刻、寺院道观和建筑构件来诉说闽都的风流。
这几乎注定了如下普遍的判断,闽都近代以来的地标,当属挨着“三山”的三坊七巷。里头走出的林则徐、沈葆桢们,深度参与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,面对晚清的落日余晖,他们倔强地力挽狂澜,在激变时代刻写下闽都子弟特有的智慧、品格和担当。作为城市人文史至为浓墨重彩的一章,当然值得大书特书。
不过,他们终究无力挽住一个时代向极坏处沦陷的颓势,科举取士的废止、大清王朝的崩塌,不由分说地将他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逼回到院墙之内。
有能力收拾金瓯、重建政制的是借道东洋或取径苏俄的另一拨人马。循旧例援旧制地建功立业不再成为可能,蓬勃的行动因而偃旗息鼓在个人的内心,吟花弄月或者孤独终老。
当他们意识到无缘且无力于崭新的事业时,时代巨大的喧嚣已经毫不客气地撞开了这座老城的中心,往离心方向奔拽的缰绳正越拉越紧。
历史因而既是时序的变动,也是空间的推移。
自北向南延伸的榕城中轴线上,有上下杭边的码头商埠,挨着喧腾的世俗生活唱响商业经,串连起内部和外部;有与之隔江相望的烟台山上林立的领事馆,异域风情在钢琴声中如潮水一般弥漫,贯通着近代和现代;有长安山下的协和大学,让外来的欧风美雨和本土的格物致知互为激荡,构造着全新的智识系统。
然而,长安山既没有上下杭的热烈,也没有烟台山的烂漫,只能以特殊的方式投身于又超然于这座城市、这个国度发生的一切,它的性格的养成虽迂缓慢但有序,并有迹可循。
从更大范围的地理特性来看,人们或许会暗自惋惜,长安山不够挺拔的高度,被立在城市东西两端的旗山和鼓山压抑,更被蜿蜒于闽省西北部的武夷山脉遮蔽,这多少妨碍了它的声名和形象的传衍。
人们或许还会暗暗思忖,莫非这是十来年前长安山将大部分的人员和物资转运到旗山脚下,另辟新基的原因?
真实的缘由是,当年,为了资源的整合与共享,长安山下的这所大学,不得不和国内绝大多数大学一样,奉命开疆拓土,建设大学城。
十年树木的时光如白驹过隙,这处新址虽已绿树成荫,可是,走在一马平川的新校区,人们当会感慨,任凭校园的面宽豪阔校舍括新,来不及沉淀的依然是一种须臾不可离的传统和传承的氛围。
毕竟,十年树木的时光之河太浅,就像在它边上轻易滑溜而去的溪源江。
毕竟,旗山是无从更亲密些倚靠的背景,新校区无法像长安山的校舍那样依山而建,将它全心全意地托付给山的臂弯,并让山的气息无间距地流溢到朗朗书声中。
长安山始终在耐心地等待它的孩子们归来。
最近几年,好几个学院终于从旗山回迁,以图充分用好这片被命为旧校区的地盘。这些学院是有福的。
当人们循着现代作家叶圣陶的足迹,大概会揣测,长安山和它周遭区域的风情,曾以何种方式安抚过他的心灵?
他十年之后的名篇《多收了三五斗》,其间流溢的愤然和内抑的省思,可曾有长安山深沉之品格润物细无声的痕迹?
作为客子,他又曾以何种心境投注到这里的一草一木?
精研中国古典文学的郭绍虞也曾在这所大学任教,其时山脚下已然可观的善本古籍藏书,曾散落他多少批阅华章的光阴?
萦绕着黄卷的青灯,它的微光又曾在多少个深夜一次次地息影在这片山间?
时代虽然在更广阔的空域走马灯式地为各色主角迎来送往,长安山下却愿意在“无用”的致思中沉湎,尽管它并非总是安宁的。
但是,长安山的相思林可以作证,融合岭南画派和闽地画风的当世山水画名家宋省予,当他在山上春去秋来的四时变化中挥毫泼墨,这些精神气质飞升于山形地质、摹本超拔于底本的今世珍品,不正是像法国后印象派巨子塞尚那样,对地理上不足为奇的圣维克多山的铺衍,实现了山和人的相互成全,进而彰显出一段画史、一方水土的辉煌与灿烂么?
这并非暗示,长安山惯于锁闭自身,对象牙塔之外的市声充耳不闻漠然视之,不如说,面对整个世界日益深刻的世俗化进程,它不只要追怀和检视过去,更要拥抱和陶染现世,以此作为现代大学的根本使命。
这也决定了长安山文化与烟台山文化的差异,后者以领事馆的风姿浸透到各色“庐园”建筑之间,可是,哪怕像位于马厂街的接纳过民国作家林徽因的可园,哪怕像位于程埔头的国民党主席林森的公馆,也已随着历史烟云的远去不可逆转地走向寥落、萎顿和衰败。
声明:本文由入驻焦点开放平台的作者撰写,除焦点官方账号外,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,不代表焦点立场。